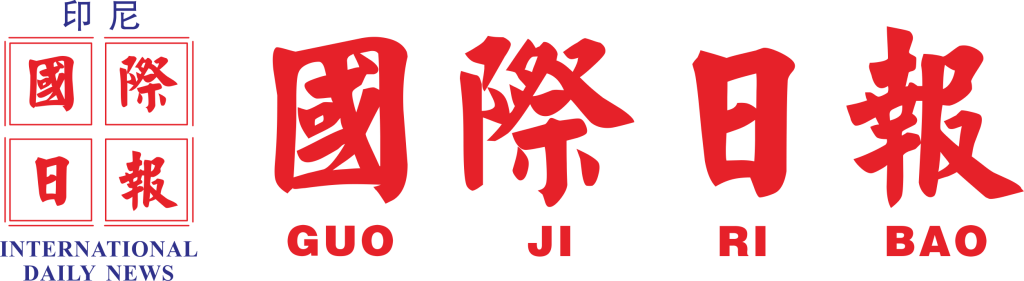亨德罗·威彦托(HENDRO WIYANTO)
这件事之后,达当被母亲寄养在他万隆的阿姨家里。陈益洲离世所带来的经济压力,迫使他还在就读小学二年级的姐姐辍学打工,以帮补家里的经济。
“我的姐姐至今未婚。她是我们家的一道护身符。”达当有一次这样说道。在学校里,同学们都叫他印(尼)共小崽子。这样的言语令小达当惶恐不安,时常哭泣(采访,2002 年4 月4 日)。
2002 年,在雅加达文化先锋(Bentara Budaya Jakarta)展览馆举办的、以《无法言传的恐惧》为主题的独立展览上,达当说出了这个埋藏在他心中达数十年的秘密。
他说:“在新秩序时期,我不想说出这个秘密,因为这等于自杀。我不想毁掉我自己。但是,终有一天我会说出来的。如果孩子们问我:爷爷是寿终正寝的吗?他的坟墓在哪里?我不可能一直对他们撒谎,这对我们自己来说是不健康的……这种腐朽的精神状态一点都不健康,这个令人作呕的谎言我再也不想继续遮掩下去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情况对我来说是一种能量。一种拒绝屈服并被法西斯政权击垮的能量。沉默难道不是等同于默许吗?”
“我希望,我的作品背后的事件能够成为自我治愈和社会康复的对话。此外,也能够成为研究艺术作品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桥梁。”(采访,2002 年4 月9 日)
他在这个展览上的作品《红雨》(2000 年)是一个以大约1965 根的红色羊毛纺线为主要元素的装置艺术作品。这些纺线垂下来触碰到地板表面,就像从画廊的天花板落下来的血雨。纺线的一端连着一幅幅形似头颅的、漂浮在空中的画。在这些人类头颅的额头上,我们注意到都有一处醒目的黑色擦痕。而纺线的另一端则被揉成一个个红色线团,垂在地板上彷如数以千计的红色斑点。
达当使用红黑两种颜色来表现心理创伤和一段烙在我们记忆中的灰暗历史。他用一截明信片大小的、华人传统祭祀中使用的元宝纸,来充当头颅画作的介质,以祭奠已逝的灵魂。不过,《红雨》实际上是达当特意为父亲而创作的一种无言的祈祷。
从达当近几年的其他作品来看,他的艺术风格越来越趋向于叙事和个人背景。同时,也表明他在政治历史和社会生活中所观察到的暴力现象无处不在。
譬如说,他的装置作品《他们作证》(1996-1997)是一组真人大小的、怀抱受害者的各种遗物的证人雕像。毫无疑问,这些雕像都长着华人面孔,对此艺术家本人如今已公开进行了说明。关于这段隐藏长达数十年的家族历史,达当表示,对他来说,1998 年之后的时期正是重塑自我的最佳时机。
1999 年,达当携妻子尤丽娅娜·谷苏玛斯杜迪(Yuliana Kusumastuti)和古侬(Gunung)、恩本(Embun)两个孩子移居澳大利亚,在达尔文市的北领地大学(Northern Territory University)的艺术设计学院教授装置艺术课程。在这个全新的居住环境里,他开始创作一项名为《计算受害人数》的艺术作品。达当估计,20 世纪世界各地近2 亿人在各种暴力冲突中死于非命。这项《计算受害人数》的艺术工程至今仍在创作中,尚不知何时结束。
关于他的艺术态度或观点,达当如是写道:“让艺术家们拥有构建理性社会的意识形态吧,而不是倡导安装炸弹杀人的意识形态,或通过同样血腥的意识形态与恐怖分子决战。艺术家的意识形态不偏颇于任何一方。”(电邮采访,2002 年4月9日)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未完待续)




采访他的母亲,2005-1024x641.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