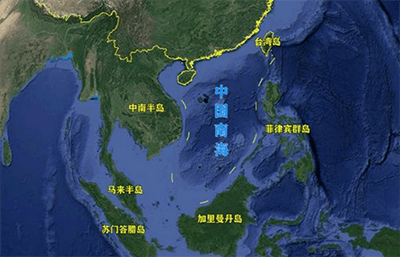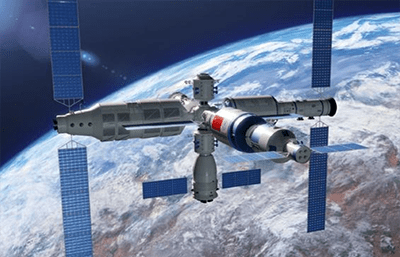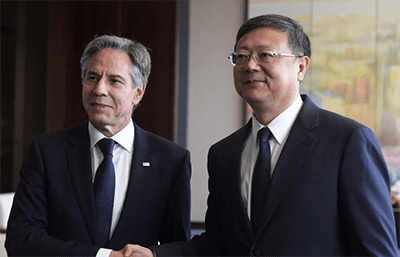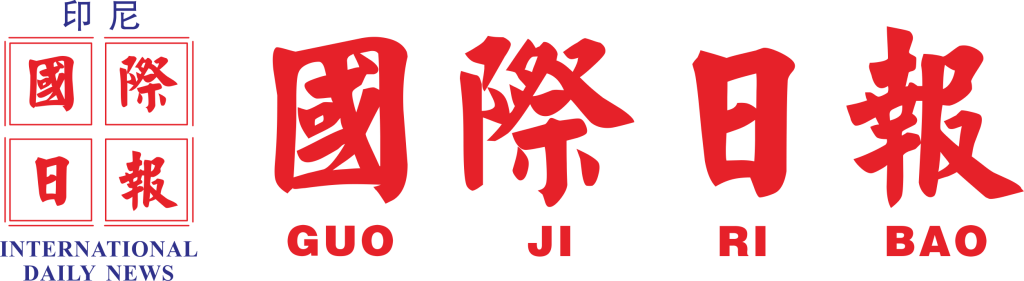阿夫(上篇)
大妹特地到雅加达来,说是约了五十多年不见的小学同学,要在同乡聚餐会上见面,并要求我陪同。为确保我不会拒绝,她还特意加了一句:“听说阿夫也会出席。”
阿夫也出席!大妹那一句话触动了我,也勾起了我的记忆,让我又想起了阿夫,想起与阿夫共度过的时光。
阿夫其实不叫阿夫,老师叫他赵国富,准确地来说,他应该叫阿富才是。但“阿富” 这个名字从他父母口里用粤语叫出来就成了“阿夫”。于是,大家也就跟着把“阿富”叫成了“阿夫”。
阿夫家和我们家后门相望,中间相隔一片混凝土地和一口公用井,我和阿夫从小就是共饮一个井里的水长大的。阿夫他们家里兄弟十人,阶梯似的。我至今也没搞清楚阿夫到底行几。但我喜欢他们家热闹,常赖在那儿玩,高兴时就留住一宿,与十兄弟并排睡楼板。
阿夫家门前开店做生意,卖汽车零件,很有点钱。他爸爸每次从棉兰办货回来,总会让长途客车停靠在他们家店门口,卸下好些个用装火炭的竹笼子包装的红毛丹,而阿夫就会拎着其中一个送到我们家。
阿夫兄弟学习成绩总不理想,每个学期结束派成绩单,阿夫妈妈便手持藤鞭在家里候着,成绩单取回家后,家里便是一片鬼哭狼嚎。左邻右舍在嚎叫声中就知道他们兄弟中哪个不好彩,今年留级了。
阿夫运气还算好,年年侥幸过关,但他也曾经嚎叫过两次,第二次的惨叫声过后,新学期他就坐进了我们班,成了我的同桌。
阿夫与我性格迥异,我爱呆家里看书,他爱在外胡混。阿夫对黑道消息和街头混混的底细了如指掌,谁属哪个帮派,谁欺软怕硬,谁靠人多势众,不敢单打独斗,他都摸得一清二楚。阿夫从不理会不准夜出的校规,常在电影院门口混到深夜,有时鼻青脸肿地回家,便又遭来他妈妈的藤鞭伺候。
我自以为书读得多,很懂得些成语,看阿夫这付模样,便很自以为是地把他定义为“一介莽夫”,而我却自诩为“一介书生”。令人难于置信的是,莽夫和书生竟然也可以水乳相融,和谐共处。
阿夫的语文不行,上作文课时总求我。偶尔上课我们偷偷用练习本聊天,他写一句我写一句,他的错别字离谱到都叫我忍不住笑出声来了。但阿夫却是体育老师的爱将,百米跑没人能赶得上他。打鸟上树,他更是能手。
邻居“大地主”家后院种着些果树。阿夫领着我去采果子。我们偷摸着穿过破篱笆入了院子,他轻轻一跃就上蹿到了一棵树的顶端,我费了很大的劲才爬到树腰。见我在他底下战战兢兢,阿夫咬着刚采到的青涩果子,很得意地在树顶上唱起了歌。唱得高兴,又转身背朝下的把四肢挂在树干上,用力晃动树干来吓唬我,见我没反应,他又用客家话朝着大地主的屋子,怪声怪气的叫将起来:“阿PAK ME(伯母),有人上你的树!”叫得兴起,树干也越被他撼得更狠。殊不知那棵老树经不起折腾,只听树底下“喀喇”一声响,树干竟然在底下爆裂,整棵大树便也在沙沙沙的树叶摩擦声和喀喇喇的断裂声中徐徐往下倒去。我被吓蒙了,不知所措地望向阿夫。就在倒下的树干快碰到地面的刹那,阿夫这才大叫一声:“跳!”我没多想便纵身一跃。好不容易在地面上站稳腳跟,惊魂未定,就见阿PAK ME提着长棍,满脸怒气地从屋子里冲了出来,对着阿夫就是一棍子用力抡了过去。阿夫闪身避让,向我吼道:快跑!我跟着阿夫拼命狂奔,阿PAK ME在身后咬牙切齿地追赶,尖声叫骂。我跑得面青唇白,阿夫却边跑边兴奋地在狂笑。
抓鱼的季节,我又无辜地被拉了去。见我同行,小伙伴们都觉得不可思议,都不相信阿夫有这本事,把个书呆子给骗出来跟着他们胡混。
在郊野的小溪,大伙儿光着脚踩在水里,聚精会神的分头捞鱼。突然,我觉得小腿肚上有些什么不对,回头一看,好家伙!竟是一条大蚂蝗牢牢的吸在后腿肚上,我忍不住惊声呼叫,这一叫竟把大伙儿都惹得大笑起来。阿夫也笑骂着说:“真没用!就一条林带(Lintah, 蚂蝗),看把你吓的!”然后从口袋里掏出根香烟,撕出烟丝揉碎了压在蚂蝗身上,再轻轻一把将它拉下。鲜血从伤口淌了下来,阿夫也不怕恶心,竟然吐了口唾沫用手涂在了伤口上。
回来后众人拿此事说笑,阿夫看着不太高兴,沉声对我说:“去把你捞的那条鱼拿出来给大伙儿见识见识。”然后他指着我取出来那个装男用发腊的旧瓶子,问道:“你们有谁觉得自个儿捞的鱼有这条好,不妨拿出来比试比试!”不知是被阿夫,还是被瓶子里那大张着蓝鳍紫腮,霸气十足的鱼给威慑住,现场竟然一片沉默,没人言语。此后也没人再拿蚂蝗说事。不过,当时我和阿夫心里都明白,那条鱼其实并不是我捞的。
那天我在戏院门口买竹筒糕,突闻街角一声喊:“在那儿!”接着就见几个小流氓往我的方向指,并气势汹汹地朝我冲了过来,还未及反应,我左颊就先挨了一拳,紧接着后背又挨了几个拳脚。在那紧急的当儿,我急忙转身,把刚买到手那两包热气腾腾的竹筒糕朝那群人的脸用力砸去,然后拔腿便跑。他们被砸了一脸,更气得发狠地追了上来,我一口气跑出了几条街,跑得气喘吁吁的,他们竟然还紧跟在后面追赶。我越跑越接不上气,感觉快虚脱了,而他们还在穷追不舍,看似不逮着我就不肯罢休。就在我惊慌绝望之际,横地里蓦地杀出一条人影,截住那帮流氓。我喘着气停步回望,只见阿夫只身挡在四个混混面前,赤手空拳的企图阻挡他们的追击。我调整着气息,看着阿夫拳来脚往,阻东击西的以一敌四,很是威猛,但毕竟他单枪匹马的,眼看还是寡不敌众,三两下子又见挨了几下拳脚,我看他渐渐的难以招架,想着他这是在为我挨打,便心一横的冲入战围,两人联手对抗四个小流氓。几十个回合下来,我发现我们的确是势单力薄,难以取胜,便低声对阿夫说:“估计是打不过。”阿夫果断地回应说:“准备撤!”说着便急速旋身,左右交替,连续地狠扫出几记连环腿,我也快速出拳,使尽力气配合阿夫强逼对方后退。听到阿夫一声:“撤!”我俩同时抽身,疾走逃命。
两人全身挂彩各自回家。在房里清理伤口时,我听到后门口传来撕心裂肺的嚎叫声,然后是阿夫妈妈气急败坏地叫骂声。我走到阿夫家后门口观望,只见阿夫在地上边滚边叫,他妈妈不停地往他身上抽鞭子,边抽边骂道:“为什么又打架?再不说看我不打死你!”
看见阿夫那副惨状,我忍不住走进屋里,对阿夫的妈妈说:“我知道他为什么打架!”我的突然出现让阿夫妈妈有点意外,她停下鞭子看着我。“阿夫是为了救我!”我告诉她。
看着也是鼻青面肿的我,阿夫妈愣了半天,张张嘴不知该说什么。随后,她摇头叹了口气,扔下鞭子进了房。我弯身一把将阿夫拉起,将从地上拣起来的鞭子在他面前扬了扬,问道:“被打得够呛吧?”
“还行!”他不以为意地咧嘴一笑,看着他身上的鞭痕和那一副蛮不在乎的样子,我也乐得忍不住笑地揶揄他说:“哟!敢情刚刚那声声惨叫是我的幻觉?”
“叫得惨些,鞭子便少挨些。哎!这事你不懂。”说完他嘎嘎嘎的笑。
火车道旁坡底下,有一大片隐秘在灌木丛后的青草地,当中横着一条小溪,还有好几棵高耸入云的椰子树。也不记得我们是怎么发现这个世外桃源的。放学后,我们常常穿过灌木丛,把书包扔到草地上,围着椰树干互相追逐,跑进溪里嬉水。在树底下斗鸡尾草,有时会静静躺在草地上,看着天上的蓝天白云,说着不着边际的话。阿夫和我都很喜欢这个地方,我便提议该给它取个名字,阿夫说取名这码事他外行,只能我来。我望着天上的悠悠白云,突然想起一首歌的歌词,“朵朵白云飞向我的故乡”,觉得很是诗情画意,便问阿夫:“你说,叫做‘故乡’如何?”阿夫拍掌大笑,说:“这名字好,够文艺。”
“你拉倒吧!”我推他一把,“你一介莽夫,懂什么‘文艺’?”
“我一介莽夫,那你是一介什么?”
“我一介书生!”我说。
“哈哈,就是一介书呆!”他又拍掌大笑:“一莽一呆,还算般配!”
我被他这无厘头的串联逗得忍不住,也跟着大笑起来,我们越笑越响,越笑越凶,笑得停不下来,最后两人都在草地上滚。
阿夫似乎对“一介莽夫”这个称号感觉满意,此后便习惯了开口就先来一句“我一介莽夫……”或“你一介书呆……”。
突然的动乱,驱赶华人,我们被驱离了故乡,也连带失去了“故乡”里的青草地、溪水、狗尾草和蓝天白云。莽夫和书呆从此各走各路,再无交集。
阿夫(下篇)
酒席未开,宴会厅里一片喧哗,赴宴的乡亲们满场寻找旧年相识,三五成群地围成小圈子在聊天。我和大妹跟小学同学,儿时邻居重新认识,相互交谈,大家都显得异常的兴奋。但50年的时光不算短,当年的黄毛小子和小丫头都已改头换面,不复当年模样,成了另一个人。眼前的人其实就是刚认识的新朋友,一个中老年人,很难再跟当年的同学或玩伴相互关联,因此,大家的交流看似熟络其实陌生,看似无拘无束其实带着客套。半个世纪的光阴足够改变世界。
时间到了却未开席,他们说还在等人。
这时,远处一小群人谈笑风生的步入大厅,周围的喧闹声蓦然低了下来。大妹走到我身边,低声说:“说是阿夫来了。”
走在那群人中间的那位,看着身材健硕,精神抖擞,在他身边跟着一位高挑挺拔的清瘦帅哥。我远远一看便确定中间那位就是阿夫,心里一跳,他们就已经走到我面前,拐个弯正要往前入座。我一步上前,伸出手叫了一声:“阿夫!”
他们停下步子。阿夫转头怔了一下,看着我,伸手和我相握,却有点不知所以。
“还记得我吗?”我问,握紧他的手。
他举起另一只手,边仰头思索边对我晃动着手指头,不确定的开口问道:“你是……班让(Panjang /高个子)的儿子?”我一听就愣住了,这话听着怎么好像我老爸才是他老友,而我,是他老友的儿子?我还期盼着他叫一声我的小名,然后来个开心的拥抱呢。
我们的手未及松开,一旁的人就推拉着他往里走,说:“先入席吧,时间差不多了。”推他的人转头连连摆手向我道歉:“不好意思,没时间了,散席后再聊吧!”
我还真没料到这场会见竟是这样的场面,心头惘然若失。阿夫不记得我了么?可这不该是阿夫的性格啊!但毕竟已经是50年的光景,没人能担保谁还能记得谁。况且离别后各人走着不同的道路,我朝八晚五的平稳过日子,多的是时间去风花雪月,怀古思幽,阿夫或许长年在商场拼博,整日面对尔虞我诈,生死存亡,没有闲情去怀念旧情,也是常理。其实就算阿夫真的不再记得我了,我也没有理由去责怪他。
席间,阿夫虽万般推辞却还是被强请上台致词,短短数句的发言,风趣幽默,大方得体。他从台上走下来的时候,我看见了他满脸的自信,一颗悬着的心也落了下来。他被推上台时我还担心什么来着?“一介莽夫”原来口才了得,我哑然失笑了,为当年把他定义为“一介莽夫”而笑,笑自己的鲁莽。
散席后我和大妹无声地往门外走,突然后肩被轻拍了一下,我回转身,对上了阿夫那双炯炯的眼神,他望着我,声音沉稳的说道:“不好意思,刚才进来时太匆忙,一时没料到会碰到你。”
“没事!”我轻声回答。
“一别至今,你还好吧?”他问。
“好!你也好吧!”他点点头,拉过身边的年轻帅哥,说:“我儿子!”然后对着小帅哥说:“叫叔叔!”
年轻人向前微倾了一下身子问好,说:“刚刚吃饭时爸爸告诉我,说叔叔您是我爸小时候最要好的朋友。”
“是很要好的朋友。”我笑着点头。
“刚刚坐在席上时突然想起,就跟他说了些过往的陈年趣事。”阿夫笑笑说。
“你们真的曾经几次联手把那帮坏仔流氓打得落荒而逃?”小年轻不可置信的看着我问。
我望向两鬓泛白的阿夫脸上那一抹颇有深意的笑容,忍不住也跟着笑了。
“我爸真有那么厉害么?他看起来连我都打不过。”小年轻捉狭的看着他的爸爸。
“他那是疼你,舍不得打。”我说,“你爸当年确实英勇,他救过我。”
“已经是陈年往事了,感觉还像昨天。”阿夫脸上闪过一丝怅惘。
“都半个多世纪了,”我说,“真快!”
“是的,我们都老了。”他笑,额头眼角有不少刻纹,“就不知我们的‘故乡’是否还在?”
“在的话,或许也早已荒芜,杂草丛生,或许溪水干涸,椰子树也都不剩了吧!”我轻叹。
年轻人一脸疑惑地看看我,又看看阿夫,我和阿夫看着他那副模样,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这些年,你们一家都过得很好吧?”阿夫又问。
“都好!真的都很好。”我说。我们四目相投,突然不知道该再说些什么。
这时,几个人急匆匆地走了过来,一见阿夫便大声嚷嚷:“大家到处找你,原来你还在这儿,快!都在车上等急了。”说着拉了阿夫就要走。
阿夫紧紧握着我的手,说:“我还有事,再联络吧,找个时间好好叙叙旧。”说完转身要走,忽又回过身子对我说道:“刚发的本子里有我的联络号码。记得联系。”
“一定!”我说。
阿夫被强拉着走了,刚走两步又回转头对我说了声:“再见!民!”
在那最后一声“民”里,我听出了五十年前的味道,那正是五十年前的声声“民”。突然的,我感到心头拥塞,又感到一股热流往我头上蹿,有点眩晕。
前方,那渐走渐远的背影瞬间即成了一片朦胧。
半晌,一直默默站在身边的大妹碰了碰我的手臂,盯着我的双眼轻声问道:“是不是该走了?”
我偏过头,偷偷擦了擦眼角,轻声说:“是该走了。”
不知怎的声音听着竟然带点哽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