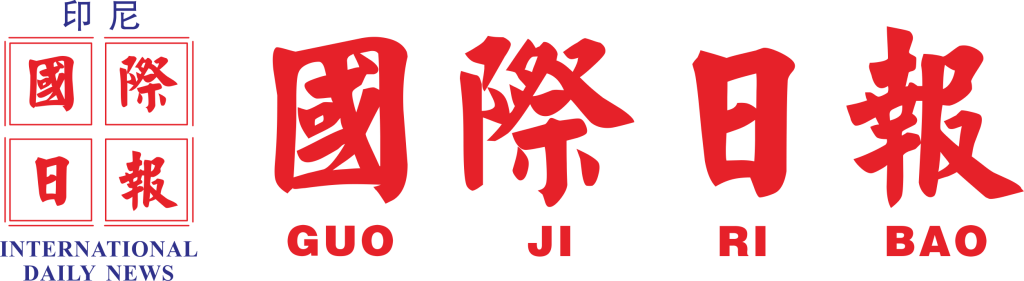玛丽·索默斯·海杜丝 (MARY SOMERS HEIDHUES)
中国科技在印尼乃至东南亚地区的传播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反之亦然。不过,我们很难详细说明这种交流所带来的影响,特别是探究其发生的确切时间和地点,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如果想要找到真实的信息来源,从纷繁复杂的传说中甄选出真相来,可能需要侦探般的思维和敏捷度。再说,即便某些来自中国的技术可以传播到印尼,但很大一部分仍局限在华人居住的地区,成为华人安身立命的技能。即便如此,也有一些创新为当地居民所吸收和接纳,如今成为印尼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
本文将列举几个华人在印尼基础科学与技术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并简单探讨一下其影响、融入当地文化实践的时间及局限于传播群体的程度。如果没有能够融入当地的习俗,那么原因何在。如今,在知识全球化的大环境中,印尼华族将全球性科技引入印尼也同样功不可没。
烹饪术语
这一部分探讨印尼日常生活中应用广泛的食物和物品,简单的追溯方法就是在印尼语当中找出华语借词(Leo,1975; Kong Yuan Zhi, 2009:301-316 ; Lombard, 1990),特别是源自福建话或闽南语的词汇。倘若印尼语中有许多常用的词汇被公认为华语词汇,那么这些词汇极有可能都来源于中国,并在努山达拉群岛(Nusantara)上经过借用和适应的过程,从而形成如今的面貌。
孔远志(Kong, 2009)将印尼语中发现的454个华语借词分成十一类。其中,食物或食品类的词汇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为频繁,也最为常见。此外,诸如中国宗教和风俗习惯的词汇(如Toapekong大伯公,capgomeh十五夜即元宵节)、对朋友和亲属的称谓或者各种游戏名称(尤其是赌博)(Kong, 2009:308-309)都广泛应用于华人社交圈,其意义也为当地社会所认可(详见本书第二部分《印度尼西亚语中的汉语借词》)。
上述大部分华语借词都与黄豆及其加工工具有关,或可以称之为“食品技术”。tahu(豆腐),是由黄豆发酵而成的。或许,这是最古老的、迄今仍为人们所知的外来借词。人们在10世纪初的爪哇古碑文中发现了tahu(豆腐)一词,但直至19世纪初,这个词才流行起来(Jones, 2009:161;Lombard, 1990:225)。后来,出现了一些派生词,如tauge(豆芽)(多指绿豆或黄豆制作出来的)和kecap(酱油)(Jones, 2009),均由黄豆加工而成。当地人还将这种技术发扬光大,以整粒黄豆为原料制作出了豆酵饼[1](tempe),显然为世界食品多样化作出了真正的贡献。
另一类是带有面条之意的词汇如mie(面条)、bakmi(面条),bihun(米粉线)和kuetiau(粿条)等等,都是印尼语中食品类词汇。这类食品是以米粉或面粉为原料,被揉成面团后加工成不同形状。这也是一种食品加工技术。如果将面团加工成不同形状,放在锅上蒸或烤,就可以制成kue(糕点)。Kue是华人用来称呼糕点的词汇。此外,从速食面的风靡程度,我们还感受到印尼人民对Mi(面条)的无限热爱之情。这些都是由中国传入努山达拉群岛。
华语借词ciu(酒)通常是用来称呼米酒(Arak,rice wine),而另一含有“酒(Tuak,Wine)”之意的非华语词汇anggur则指的是葡萄酒。当ciu(酒)变酸(且不含酒精)后,就变成了cuka(醋)。Cuka(醋)是另一来源于中国的词汇。17世纪,巴达维亚(Batavia)城郊是华人糖厂和农民聚居之地,在这里出现了几家华人经营的酿酒厂。自元朝(公元13-14世纪)起,中国就发明了蒸馏提取技术。这些工厂以米、糖和椰子为原料,发酵酿制成酒。这些酒除了自用之外,更主要是用来满足欧洲市场的需求。荷兰东印度公司(VOC)定期将上述大多数酒出口到荷兰(Lombard, 1990:223)。
酒是一个例外。华人将酿酒技术引进印尼,但当地人并没有选择去学习这门技艺,因为穆斯林禁忌饮用酒精类饮品。至少,当地人酿酒并不普遍。另一方面,茶是华人引进印尼的另一种饮品,同样经过发酵制作而成,并且不含酒精。正如罗德里奇·巴塔克(Roderich Ptak)所言,茶在印尼社会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一些地区的人民马上种起了茶树。到了20世纪,特别是受到瓶装苏打水的启发,印尼人民还充满创意地生产出一款用华语命名的特色饮品 teh botol(瓶装茶)。
这些源源不断被制作出来的大多数食品,都为当地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在当地食品中,各类豆制品是当地人摄取蛋白质的主要来源,也是烹饪印尼美食不可或缺的材料。更为甚者,当地的烹饪方法也受到中国的影响。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中,也包括如今摆放在印尼老百姓厨房里的各类烹饪工具。如,铁锅来自中国,而印尼马来语中的pisau(刀)一词也似乎来源于远古时期的华语词汇“匕首(bishou)”,两者所指为同一物。虽然印尼有些地区生产炼铁所需的矿石,但爪哇岛上并没有铁矿。况且,有铁矿的地方,就意味着需要一定的人力去开采和加工。中国有许多能工巧匠,冶炼和锻造铁器的技术出神入化。因此,中国制造的主要用于出口的铁器极有可能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出口到爪哇,特别是在中国和东南亚的贸易往来日渐频繁的10世纪左右(Lombard, 1990:228-229)。
其他领域
厨房之外,还有许多外来词汇指向来自中国的“技术转移”。“cat(油漆)”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其他的词汇,还有与印尼华人移民活动息息相关的,方便做生意的toko(商店)、suipoa / sempoa(算盘)。在西加里曼丹岛各地,还有许多人将dacing(大秤)与华人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种大秤在15世纪的马六甲(Malaka)和100年之后的亚齐(Aceh)早已广泛使用(Jones, 2009:11; Lombard, 1990:256, 399-400)。买卖中的其他重要元素,如picis(角,一种铜币或锡币)或seng(分,一种中间带方孔的硬币)是在中国和东南亚一些地区制造。此外,人们还使用华语kowri(玳瑁)来称呼另一种更为古老的“玳瑁币”。从14世纪起,爪哇地区就出现了中国的picis(角)。如今,这些中国picis(角)虽然已经失去了支付功能,但依然大有用处,尤其是在峇厘岛(Jones, 2009:149)(详见本书第三部分《峇厘印度教祭神仪式中的铜钱》)。
另一关于技术适应的例子,就是将马车改装为印尼别具特色的交通工具becak(三轮车,马车或牛、马拉的大车)。此外,扁担及其两头的箩筐也有可能是来自中国。这两个工具让搬运变得十分便捷。虽不能说完全不费气力,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省了力气。当地人马上仿而效之。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手推车(Wheelbarrow)上。不过,手推车的使用仅限于邦加岛。在这座岛屿上,华人通过生产使这座岛屿闻名的文岛白胡椒来增加黑胡椒的种植,而黑胡椒在这座岛上早已广为人知。
郑和:一个特殊的例子
陈达生(Tan Ta Sen)(2009)在对郑和(或称三宝/三保 Sam Po)的生活背景及其在东南亚伊斯兰教传播中所扮演角色的研究中指出,这期间也发生了科技转移现象。从1405年至1435年,郑和奉中国(明朝)政府之命,多次率领庞大的舰队对东南亚地区进行考察。在此期间,可能会有许多舰队成员在印尼,尤其是爪哇地区定居下来。他们向当地人民介绍中国物品和技术,为当地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郑和是来自云南的穆斯林。早在郑和时代之前,就已经有阿拉伯、波斯及其他国家的穆斯林商人和使者在中国南方港口城市如泉州和广州定居。他们或他们后裔为这次远洋探险贡献了很多专业技能。在郑和(Zheng)的舰队中,大多数船员都是穆斯林。因此,学者们相信中国的穆斯林在爪哇岛伊斯兰教传播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详情请见本书第一部分《华人在努山达拉群岛传播伊斯兰教》)
陈达生描述了中国各个港口城市穆斯林居住情况的变迁。唐(618-907年)宋(960-1279年)时期,有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定居中国。起初这些外来者必须居住在一个叫“蕃坊”(fanfang)的专供外国人居住的区域,就像20世纪以前荷属东印度的华人必须居住在规定区域一样。因此,穆斯林群体与中国本地人往来的机会寥寥无几。蒙古族当权时期或元朝时期(1271-1368年)废除了这些区域。新统治者允许在行政管理、军队和其他领域中使用伊斯兰人才。这些阿拉伯和波斯后裔虽然深受中华文化的熏陶,但他们依然是外国后裔,甚至还恪守伊斯兰教教规。值得关注的是,他们将中东地区制作地图、药物、历法、灌溉水利技术、数学和建筑等技能传播到了中国(Tan,2009:93-95)。
这些穆斯林(也有非穆斯林)先于郑和去过爪哇,许多人加入郑和的远征舰队。与中国其他移民一道,他们带去许多中国先进技术。陈达生坚信他们将中国瓷器制作、冶金、纺织、造船、建筑、渔业、农业和医药领域的高新技术传播到了印尼(Tan, 2009:162-163; Wade, 2010:389-390)。这些农业技术、种植和农具制作的方法开始在爪哇及其它地区使用。有些移民还在爪哇岛沿岸及其它地区建造了中国建筑风格的清真寺(详见本书第一部分《中国工艺与爪哇岛北岸古清真寺的建筑》)。他们还在当地进行农业技术创新。同时,他们还将这些国家的许多产品带回中国,激发了中国人对草药、香料、海产品、奇珍异兽和原材料成为中国和东南亚之间数世纪以来的贸易产品的支柱。
陈达生略显夸张地渲染了华人的影响力。例如,他称郑和的一名船长于1413年从占婆(Campa)移居爪哇的拉森(Lasem)。在那个城市,船长的妻女们教当地人制作带有中国图案的峇迪(Batik),如今这种峇迪已成为拉森(Lasem)峇迪与众不同之处(Tan, 2009:197-203)。然而在中国,峇迪被称为蜡染,只是边境少数民族的工艺,鲜为人知。所以,大多数专家都不相信峇迪是从中国传播到爪哇的。虽说中国图案影响了拉森和其它地区的峇迪制作,但15世纪以前的历史已难以考证。
在《新剑桥伊斯兰教历史》(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一书中,韦德(Wade)也强调了中国东南部各港口城市的穆斯林群体与郑和西洋之行之间的关系。在这件事上,他与陈达生的观点有所不同。他认为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穆斯林群体不仅由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的后裔组成,还有来自占婆(Campa)的穆斯林(Wade, 2010:366-408)。
在郑和的随行海员中,马欢可能是最为出名的一个。由于他和其他几人的功劳,郑和下西洋,到访努山达拉群岛的过程得以被完好记录下来。他们大多数水手都住在这些岛屿上,尤其是爪哇岛。在爪哇岛,他们发现了一些华人居住区。根据马欢等人的记载,许多当地华人都是穆斯林,甚至在当地居民普遍不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区,亦是如此。经过一番辩论后,学者们现已承认中国商人和移民在爪哇岛伊斯兰化的初期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作为技术革新者的角色(Tan,2009:Wade,2010;Reid,010:443-444)。
深入的影响
到了16世纪和17世纪,中国与东南亚之间采用易货贸易模式,中国用轻工业产品换取南方各国的原材料和天然产品,以满足消费需求。例如,中国生产一种金线,可以用来织造马来统治者喜爱的、华丽的松革布(Songket)。这种金线可以用金豆或金条等产品进行交换(Heidhues, 2008a:36-37)。随着中国的日益富强,中国国内对金属和其他产品的需求也日趋高涨。同时,成品的贸易额和出口量也不断提高。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包括印尼的大部分地区,人口稀少,没有足够的劳动力用来加工数量如此庞大的原材料(特别是金属),无法满足中国的需求。因此,中国开始向东南亚各国派遣农业和矿业技术工人(Reid, 2011:21-36)。为了方便工作,这些工人还携带了新的机械设备来到印尼。
16世纪末和17世纪,第一批华工到达西爪哇,进行胡椒种植和制糖。隆巴(Lombard)辨别出一些他们从中国带来的、用于耕种的简单机器。例如,由轮子驱动的、用于灌溉的水利泵,还有由牲畜力气带动的、用来碾米或榨甘蔗的碾磨(Lombard,1990:15-216)。后来,当地人也采用这些设备来灌溉稻田,节省了许多劳力。还有上文所提及的,华人将酿酒技术传到印尼,这些米酒是由大米蒸煮后加入糖和酵母提炼而来的,主要用于出口。
华人与采矿技术
中国技术传播的另一个领域是金属开采和加工行业。由于锡矿开采备受瞩目,且有着相对完整的记录,我们再一次以锡矿开采为例。18世纪以来,中国工人下南洋,在印尼一些矿产丰富、人烟稀少的地区如邦加岛和加里曼丹岛(发现很多矿源,但采矿加工的工人却非常少),以及东南亚的其他地区开采锡矿。他们提高了当地锡矿和金矿的产量,开采出来的锡和金大部分出口中国市场。
数个世纪以来,东南亚当地人都使用简陋的方法来开采锡矿。由于锡矿通常比较接近地面,人们在寻找锡矿时会选择一个有希望找到矿石的地方,然后在那里挖个洞。矿工们通常是两人或三人一组进行工作。如果发现矿层状况良好,他们会把洞挖大,挖成地下隧道的样子。不过,这样的隧道有很多问题,通常很危险,因为不稳定而容易发生塌方事故。地下水和雨水通常都淤积在矿洞里,需要用桶将积水和多余的泥土运到洞外。最后,需要不厌其烦地用水反复筛滤矿石,因为清洗一次几乎没有什么效果。通常人们使用邦加人称为木盘(Dulang)的凹形锅来清洗矿石。冶炼技术则是借鉴一般的炼铁方法。在邦加岛,尤其是在勿里洞岛上,人们都使用这种方法来冶炼锡矿石。即便如此,采矿实际上只是矿工们的一种兼职,他们会在需要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中断挖掘工作。
一些中国移民沿用类似的方法,我们称这种方法为“东南亚式采锡或采金法”。然而,到了18世纪中叶左右,华人开始在邦加岛上进行规模更大更深入更持续、同时也更加有利可图的锡矿开采工作(Heidhues,2008b:11-12)。
1812年,美国自然学家托马斯·霍斯菲尔德(Thomas Horsfield)代表莱佛士(Raffles)到邦加岛视察。他记录了岛屿的情况,并说明了中国技术是如何提高锡产量的。
霍斯菲尔德(Horsfield)简要概述了华人所带来的变化。这些被他称为阿成(Assing),如今被称为Un(Oen温)或Bun(Boen温)的华人,很有可能是在18世纪中来到这座岛屿上。正如霍斯菲尔德如下的解释:
……他来自中国……熟悉矿石采集和金属提炼过程…还根据那里使用的模型制造了各种工具和机器,传授有关采矿、运河或沟渠各种工程中对水力的使用,制定了各种金属的形状和重量标准(Horsfield,1848:310)。
这些革新者拥有一支矿工团队。他们首先在发现矿砂的地方挖洞,这些洞要比之前采矿的洞大得多。之后,在河上建水坝,通过一个大水沟将水引到开采地点,以便将矿洞里多余的土或淤泥运出洞外。为了解决矿洞里的积水问题,矿工们使用了中国著名的农业工具——木制排水设备。用水力推动水轮从而带动与之相连的排水轮把洞中的积水排出。正如霍斯菲尔德(Horsfield)所描述的那样:
他们使用华人发明的水泵将矿洞里的积水排出洞外(在各种旅华游记中发现的描述)。这种工具由两股水流,或者由一个工人用脚踩动轮子来带动。水泵的构造很简单,由一定数量的、大小相等的矩形小木板组成,这些小木板置于一个倾斜在矿山之上的长木槽中,然后通过轴连接在一起,连接到链条上……每一块木板凹处都会舀起或搅动少量的积水,以至于在矿井底部的积水中形成一股水流(Horsfield,1848:811-812)。
在中国,这种水车是用来灌溉稻田的(详见Heidhues,2008b:19,图2),但没有任何记录显示那里的人在采矿时使用它。这种用于采矿的改良水泵似乎是东南亚华人的一种创新,或许只发生在邦加岛上(Jackson, 1969:28-54)。在这种情况下,轮子和泵用水力取代了人力。
离开(水车)大转盘后,水会流经一个水槽或水闸。这是一种三面长木盒子。矿工们将含有矿石的泥土扔进水槽中,用锄头或铲子借助水流将多余的泥土筛洗干净,然后等优质的矿石沉到水底后捞起来进行冶炼。
冶炼也是借鉴中国的方法。在东南亚地区,当地人发明了竹制风箱,由一名男子拉动它,产生一股稳定气流,用于小规模的冶炼。但是,中国人拥有自己独特的冶炼方式,他们使用大风箱来冶炼锡矿石。这些大木箱或钻成中空的树干产生一股更强的气压,提高了熔炉热量。在邦加,树段制作的大风箱需要一组人,而不是一个人来操作,他们通宵达旦、不停地守着风箱。这种来自中国的采矿方法也对工作效率的提高做出了贡献。
为了改善采矿条件,华人还引进了其它工具设施。他们使用铁钻探测地下层是否存在他们称之为Ciam(铅)的矿产。最后,使用一种木质手推车在狭窄的道路上运输锡条(如霍斯菲尔德所报道的那样,锡条的重量现已经规范化了)。这种运输工具在邦加广泛使用,是岛上特有的交通设施。由于木制的车轮一路上发出刺耳的声音,这种工具在西方观察家的眼中显得十分原始。尽管如此,木制手推车可以帮助人们经过一些复杂的地形,而无需劳烦人力去搬运。这是更有效使用人力的另一典范(Heidhues, 2008b:16-22及插图; Horsfeld, 1848:819)。
或许,在西加里曼丹及其他地区,华裔工人在开采金矿时也使用上述一些或大部分工具。然而,由于黄金储量较小,在同一矿区工作的矿工也比较少,那些工具有时也派不上用场。这种情况也发生在一些小规模的锡矿场上,那里仅需要少量矿工,所以仍使用“东南亚式”采矿方法。在这些地方,建造水车和输送水流就太过劳民伤财了。
采矿技术的革新表明,从中国到印尼的技术转移确有其事,尽管当地印尼人由于已经拥有用作耕种和灌溉的水泵和碾米机,并没有接受这些技术。不过,木质手推车或许是个例外,但人们至今依然认为那只是邦加岛的“特色”。虽然这些在邦加发展起来的采矿技术传播到邦加岛以外的地区,但仍局限于华人之间,当地人对此似乎无动于衷。对于这种不情愿的态度,至少有两种解释。当地人已经习惯了三五成群的小规模劳作,机器对他们帮助不大,而华人则通过他们称之为“公司”的合作群体,调遣大批移民,并通过奖罚制度进行监工。公司的老板们利用债务(从中国到印尼的路费、所需设备、食物和饮料以及鸦片)、惩罚制度和同乡情谊(共同的利益以及江湖义气)来管理矿工,而当地工人则对这些套路不屑一顾。第二种原因,仅仅是因为采矿本身就是一个过于艰辛的工作。当地人可以通过从事相对轻松的耕种、钓鱼、打猎或其他工作来获得更好的收入,而华人作为外来者,则没有机会从事这些工作。除了采矿,别无他路。事实证明,大多数二代华人会从事采矿之外的工作。无论是做农民、小商贩还是采矿监工,显然他们很少有人愿意做普通矿工。
最后,还需要一笔资金将所需数量的工人从国外请来,将他们的设施装备运过来,直到可以卖锡的时候,再重新安置工人。而当地矿工则把采矿和挖矿当作副业,没有资金去投资这些高风险的工作。正如卡尔·特罗基(Carl Trocki)在19世纪初新加坡附近的华人经营的黑儿茶种植园案例中所指出的那样,矿老板们定期把物资出卖给矿工们,特别是鸦片,用来“回收”他们应该付给矿工们的工钱,以保持他们的经济利润。与让矿工们自己保管工钱相比,这个方法更加有利可图(Trocki,1979,1990)。类似的情形可能也在邦加发生。
19世纪和20世纪,采矿业发生了第二波技术革新,西方技术取代了华人发明的采矿设备。人们使用蒸汽和柴油发动机,进行取矿、抽水和运输加工好的锡石。监测器和利用强劲水力清洗矿石的巨型水管,取代了以往使用锄头、累弯腰的人力活。到了20世纪,又使用挖泥船将锡矿石从海中捞出,进行清洗,然后放到巨型熔炉中冶炼。这些机器设备的引进,为欧洲资本进军采矿业打下基础。不过,一些神通广大的华人矿老板们也引进了上述新技术。
进入20世纪,由于机器大规模取代了人力,矿工的族群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印尼本地矿工开始加入或者取代了华工 (Hiddhus,2008b;111-137)。采矿依旧被视为粗重活。然而,后来几年邦加出现新趋势,采矿业成为面向所有人的领域,许多小型采矿队使用简单的机器设备在地面或海底寻找矿石。许多华人离开邦加和勿里洞的矿场,甚至移居他处,而新矿工则从印尼各地蜂拥而至。

近代的发展
到了19世纪末,印尼各地华人企业家已经摒弃了中国的技术和设备,转而引进或采用西方的新技术和发明,包括印刷机、食品加工机、纺织机以及许多其他机械工程。近几十年来,尤其在城市,这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可以说,正是这些华人企业家与其他非华人企业家一道,将西方或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进印尼。不过,本篇短文无意于列举这些创新。
对印尼医学及其相关领域的简要回顾,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和华族从古至今对印尼所做出的贡献。医学是印尼和中国互相借鉴和学习的重要领域之一。沃特斯(Wolters)指出,室利佛逝(Sriwijaya)是早期向中国供应药品、树脂(尤其是樟脑)、草药和其他香料调味品的国家(Wolters,1967)。到了17世纪,巴达维亚就已经有了中医师(Sinse),当地华人还拥有了自己的医院(Lombard,1990:275),而华人药师则散居在努山达拉群岛,售卖中药和用当地药材制作的中草药。有些华人名流是制药大亨(Lombard,1990:276)(详见本书第五部分《草药和化妆品业》)。新加坡华人还将印尼的樟脑和桉树油制成虎标油(后来被称为“虎牌”),然后又出口到印尼诸岛。二战前,在荷属东印度群岛,这种药几乎是每家每户的镇宅良药。于是,当地华商争相仿造类似的产品,与胡文虎(Aw Boon Haw)的名牌万金油竞争。如今,中国传统医学,尤其是针灸,在印尼临床实践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详见本书第四部分《中华医药》)。
进入20世纪,许多华族人士获得机会在印尼学习西医及相关领域的知识,甚至出国留学。大多数华人毕业生不仅在疾病治疗领域,而且在印尼现代医院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面向印尼人的现代医学教育领域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详见本书第四部分《医学界的华人》)。
眼科医生叶鸿俊(Yap Hong Tjoen)及其儿子叶基忠(Yap Kie Tiong)在日惹兴建的眼科医院,特别是在独立革命时期,为当地社会大众的健康提供了保障(RSMYAP,2015;Zhonghua Wenhua, 2013)。外科医生及救灾志愿者李德美(Lie Darmawan,华文名Lie Tek Bie)(详见本书第一部分的《医者仁心,毕生的使命——李德美》)、肝脏外科医生沈德民(Demin Shen)和神经学家薛碧玉(Priguna Sidharta,华文名Sie Pek Giok)都是印尼公共卫生服务领域里赫赫有名的医生典范。
已故的薛碧玉通过教授神经病学课程及其编写的教材,为印尼现代医学培养了众多新生代医生(Suryadinata,2012年)。在制药领域里,汪友山(Eddie Lembong,华文名Ong Joe San)及其同行们致力于药物的研制,让其他国家开发出来的科学医疗服务于印尼人民(Suryadinata, 2012)(详见本书第五部分的《制药行业的动态》)。
最后,就是霍斯菲尔德(Horsfield)等人所记载的、为了适应印尼锡矿开采而改装设备的技术和知识的传播。印尼人民对华人从中国带来的基础科学技术的借鉴、适应、采用和拒绝的问题,仍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广阔领域。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